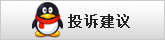
人物小传――杨佳 那是几年前夏季的一天中午,电视台的一场报告会深深的吸引了我,由此也认识了本文的主人公——杨佳。讲台上的她笑容可掬,举止文雅,不是由于听了她的报告,我很难相信她会是位盲人。
一 帆 风 顺 ―― 阳光和鲜花铺成的道路。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年仅15岁的杨佳还正在上高一。在父母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高考,很幸运的进入了郑州大学英语系。入学后,同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见她每天早晨都早起跑步,每次都跑很久,谁也没当回事,这孩子有点儿毅力罢了。第一次考试,杨佳得了第一,大家还以为是撞上的,第二次她又考了第一,大家才觉得这小姑娘有点可怕。一些年龄比她大又不服输的同学想超过她,拼命地追,但总也追不上,于是便自我解嘲说:“咱不跟天才一般见识啦”。 熄灯之后,同寝室的人经常看到杨佳床头的烛光亮到后半夜。上大四的时候,年仅19岁的她因成绩优异提前半年毕业留校,两年后她考上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来到了北京,在这里又以优异成绩留校。教硕士,教博士。24岁的时候,当上了学院最年轻的大学讲师,30岁的时候,被评为学院当时最年轻的副教授。事业成功了,爱情也翩翩而至,同样一位成功的男士走到了杨佳身边。少年得意,青年得志,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杨佳,谁也不会怀疑,她是上天格外垂青的宠儿,她人生的道路是阳光和鲜花铺就的。
黑 暗 降 临 ―― 当黑暗来临的时候,你做好准备了吗?说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杨佳觉得自己的视力有点不行了,先是上课时读课文读错行,继而又掉行,本以为是近视加重,没有当回事儿。后来在课堂上讲课时,听到下面叽叽喳喳的声音,猛然发现自己只读了半页纸便掀了下一页,就这还是没当回事,以为换副眼镜便可以解决问题了。最后还是她有次去图书馆翻目录的时候,翻了半天也找不到要找的东西,这才感到事情有点严重了。到医院进行检查,诊断书出来了,黄斑变性,失明将不可逆转,那年她29岁。杨佳不相信,她揣着诊断书又跑到另外一家医院,结果是一样的。杨佳站在医院的走廊上惊呆了。她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为什么让我失明?失明了,我怎么给学生上课?怎么上图书馆读书?是你们弄错了。”她不愿接受这个现实。杨佳从医院回来没有声张,她仍面带笑容去上课、开会,到图书馆借书。但是,当新办的借阅证递到手上,看着自己模模糊糊的照片,她的心像一下掉进了无底深渊里,禁不住泪如雨下。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残酷的打击也接踵而至,她的婚姻随着阳光和色彩在她的眼前一起溃散,丈夫提出离婚,并带着她惟一的孩子不知所踪。病眼无泪,心里却在淌血。她在讲台上坚守,不肯倒下,周末和假期她不再去图书馆了,而是蹒跚地走在求医的路上。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重复着一句话:“我的眼睛还能 治好吗?”但是,医生回答她的都是沉默和叹息。所幸并不孤单,父亲在一侧,母亲在另一侧,于逆风中陪着女儿上路。 老两口儿腾出一间屋子,把女儿接回来,杨佳说我没事,真的没事。话没说完便撞在门框上,一闪身又撞了冰箱。她一只手捂着脑门儿,一只手伸平了摸索,还笑。她竟然一点儿也看不清楚了。父母呆呆地站在一边,已是老泪纵横。 杨佳四处求医,盼着奇迹的发生,奇迹却迟迟不见。视野越来越窄,由一片到一斑,由一斑到一丝,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靠拢。终于等到那个早晨,睁眼后一片空白;大幕拉严了。没有掌声,她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真的就这样收场了么?屋里有早间新闻的声音,有父母轻轻走动的声音。母亲又起早为她熬药了。母亲为她熬了多少药?为了这些不能报销的药,母亲花去多少积蓄?她看不见父亲,却能听见他在翻报纸,又像找矿一样在找着偏方吗?母亲说父亲的头发白了,全白了。父母是为什么呢?从小到大而自己也一直是有出息又争气的孩子呀!现在,自己的眼睛永远也看不见了,怎么办?就这样变成一个让别人怜悯同情的盲人?不,我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杨佳爬起来大声说,“妈,领我去一趟图书馆吧!”
迎 接 挑 战 ―― 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失去了视力,杨佳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读书了,在图书馆里,她在书架上和卡片箱上摸索着,向她过去熟悉的一切告别。然后,杨佳笑着摸母亲的脸,买个好点儿的收录机,不读书了,我要听书。 从此,她开始一箱一箱地购买录音带,她用原声带听各种有声读物,用空白带收录电台的英语广播,录音带买得多了,店里的老板感到奇怪,这是干嘛呀?买那么多的录音带还不要发票,以为是碰上盗版的了。后来知道了原因,不胜叹息,给了她一个出厂价。一段时间后,杨佳的房间里便到处堆满了录音带,杨佳在这些带子里找到了一个声音的世界,在这个声音的世界里又找回了自己。 除了听书之外,想要著书立说,杨佳还必须学盲文。学汉语的盲文难,学英语的盲文就更难了,但是杨佳不怕,而且进步神速。学了盲文就要用,她开始准备动笔了,想写一本《研究生英语阅读》,帮助研究生渡过英语阅读的难关,那是她失明前就想写的一本书。怎么写呢?母亲用厚纸板给她做了书写框,她在上边打盲文,结果因为用不惯,字母打得叠在一起,像缠作一团的细铁丝。于是重打。就这样咬着牙练下去,原稿增增减减,积了厚厚一沓。为了写书,她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了床,早早打开收音机,夜晚12点以前没睡过觉。人也瘦得皮包骨头,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却从未阻止她。他们知道,女儿此刻正在与自己的命运交战,她不会放弃,也不能放弃。 得知杨佳的境况之后,许多亲戚朋友来家探望她。走进杨佳的小屋,大家都惊讶于这里的清贫。这是年轻女人的深闺吗?屋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连黑色的收录机都泛着灰白色。房间里连一个衣柜也没有,暖气的回水管从屋顶穿过,挂着十几个衣服架子,上面挂着她全部的衣服。然而,从门口到过道,再从过道至卧室至阳台,蜿蜒不绝地摆放着许多纸箱子,箱子里面满满地装着录音带。杨佳知道每一盒带子的位置,平时任何人都不能碰,她说一碰就乱了,一乱就不能安心干事了。新书成了杨佳的寄托,有次晚上做梦,她梦见自己写的书出版了,她举着书在人流中叫卖:“看看我的书吧,我的书写得好极了,但我自己看不到,求求你们帮我看看吧。” 叫着叫着,她从梦中醒了过来,于是爬起来摸索着,把冰凉的书稿找到贴在心口上,泪水 忍不住滴了下来。 工夫不负有心人,让杨佳欣慰的是,她用汗水和泪水凝结成的书稿,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她的导师“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夫人”李佩教授亲自为她的新书写序。杨佳满意了,她觉得自己付出的辛劳都得到了回报。
走 出 黑 暗 ―― 黑暗降临了,黎明还远吗?别人说月亮真圆,杨佳会下意识地往天上看一看;说风筝真高啊,又会抬着下巴看一看。明眼人的习惯不好改。走路也这样,鞋底趟着地走一会儿就大意了,家里挨碰是轻的,在街上撞树崴脚磕膝盖是没有断过的事。开始的时候她试着用盲杖探路,但是,走着走着,居然让盲杖把自己绊倒了,于是索性把盲杖扔了。同事们心疼她,为她在台阶边缘漆了宽宽的白线,示意她走路当心;怕刮到她的衣服和眼睛,又折断了伸到路边的树枝。后来,随着时间推移,白漆渐渐脱落,大家要为她重漆一遍,杨佳却淡淡地说,不用了。她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失明后的杨佳仍继续在本院教书,几乎没有耽误过一节课。也应邀到外校讲课。教室不一样,电教仪器的规格型号也不同。她最怕的是摸不准旋钮。不肯让学生帮忙,甚至不肯让他们知道她是一个盲人。为了不麻烦别人,她经常提前一天到教室熟悉环境,摸摸电钮,丈量一下黑板,确认一下放粉笔的位置。她依然写漂亮的板书,有谁知道她贴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地丈量着尺寸,好配合写字的右手。而为了这几行板书,她不知在家里练了多少遍:在房门上,在硬纸板上,细细体会着左右手的配合。语音教室里本来是平面的操作台上的各种按钮被她悄悄地贴上了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胶布,作为记号。她在第一节课时必定要提问每一个学生,在心里默默记住每一个学生不同的声音。下一次,她就能亲切地叫出提问的学生的名字了。她还始终保持在与人交流时专注地注视对方,事实上她是全凭听声音判断对方的位置的。36岁的杨佳开设了20多门英语课程,她的学生都是博士生。你能想象出这都是杨佳失明之后做出的成绩吗?他们喜欢上她的课,因为“杨老师发音很准,声音很好听,上课形式多样”。她上课喜欢提问,板书不多但很整齐,课上发的篇子都是很有用的课外资料。记得有一年在香港召开一个学术会议,面对失明后第一次需要独自旅行,杨佳心里也曾有过一丝的犹豫,但她相信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这个世界毕竟还是好人多。于是她毅然打起行囊上路了。每次在她过海关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时,大家都不相信眼前这位举止文雅的人会是一位盲人。每一次都会得到热心的帮助。就这样,杨佳独自一人走遍了世界许多地方,参加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1992年随中残联代表团出席“残疾人国际第五届代表大会”并在“****和妇女”专题会上作了题为“携手迈向新世纪”的发言;在世界盲联理事会上,亲自宣读了由她起草的《1990年世界盲联妇女委员会与文化委员会联合会议决议》并获得通过,应美国教育部长邀请,出席“国际自立高峰会议”。 她现在是世界残联的妇女委员(亚洲惟一的一个女性委员)。
走 进 哈 佛 ―― 人生的新轨迹,生命的新起点。2000年7月,经过杨佳不懈的努力,她接到了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惟一的来自国外的盲人学生。这位眼睛看不见,却能当博士生导师的传奇人物正在该校深造的消息通过网络传遍了哈佛。在哈佛大学,面对上千门课程,面对那么多新的信息,她非常兴奋。“想学的东西太多了。我每天一早就去听课,上到下午5点半,中午就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吃饭。晚上就在宿舍里读书、上网,往

